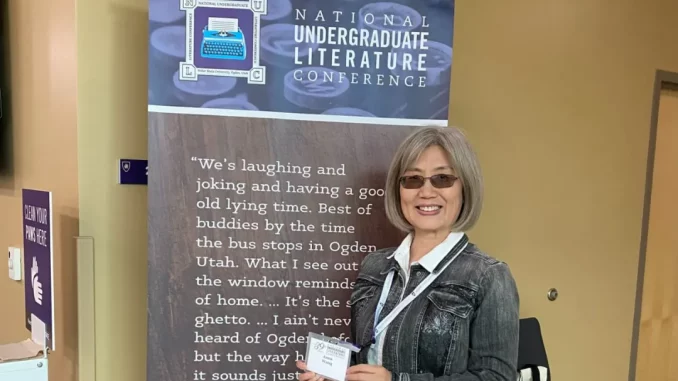
文 | 王芫 编 | Mina.L
图 | 受访者提供
作为一名“60后”,在2020年疫情期间,我决定在美国重新上一个大学本科,学英语文学。一转眼四年过去了,我已经完成学业,拿到了人生中第二个本科证书。毕业典礼那天,我女儿和一对朋友夫妻都来了。
我的朋友让我谈谈为什么要在五十多岁读一个本科?我回答说:“因为我的两个孩子在北美长大,英文都变成了他们最熟悉的语言,所以我想用英文写作,从而让他们理解我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朋友又问我女儿:“你怎么看你妈妈想为你们用英文写作?”我女儿说:“她用英文写作不是为我,是为我弟弟。我中文比我弟弟好多了。”
很明显,我女儿不买帐。后来朋友又问我女儿:“你对妈妈读大学有什么想法?”我女儿说:“没什么想法。她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她并不是因为读大学这件事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朋友非常想从我女儿那里得到诸如“妈妈是我的榜样”之类的评价,但我女儿始终没有这样表达。她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表达出的意思是:她自己就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并不是受妈妈的影响。她自己现在都读博士了,而身为妈妈的我还在挣扎着找一个理想的硕士项目。
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我们怎样做父亲》:“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
我没有鲁迅那么高尚。我看到女儿比我更强更幸福,既高兴又失落。这失落并非是因为嫉妒女儿,而是觉得她竟然连军功章的一小角儿都不肯给我。嘿,我好歹还在你博士申请截止期前给你发过三条信息,强烈要求你考博士呢!
那么我读英语文学,想用英文写作,是真的为了孩子吗?当然有真实的成分在内,但也不尽然。我并不是一个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我的前半生走了很多弯路。我经常心里想着A,嘴里说着B,行动上是C。
你相信吗?在我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我还曾经想过学医生助理。这首先是因为上学需要花钱,我对于花家里的钱学文学总是感到内疚。当时我的计划是读一年半社区大学,修够36个学分,然后转到一所本地的教会大学去。
社区大学每学分285元(美国人只需要付每学分28元),教会大学当时的学费是每年三万五,如果我在社区大学能得到3.6以上的GPA,学校每年给我一万转学奖学金,这样一算,我读完四年制大学至少要花七万块学费。
为什么不用七万块钱学个能找得到工作的专业呢?如果我当了医生助理,毕业一年就能把学费赚回来了。再遇到突发传染病等的意外,就不必再感慨百无一用是书生了——鲁迅是弃医从文了不错,可鲁迅是官费生啊。
学医生助理还是女儿给我提的建议。北美看病贵,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制度的限制。比如感冒发烧需要抗生素,就必须去看医生拿处方,而医生收费动辄几百块。为了降低成本,保险公司正在逐渐把一些简单服务下放给医生助理,力图用医生助理取代家庭医生。医生助理如今供不应求,年薪十万起步。
究竟是学医生助理还是学文学,对我的唯一影响就是在社区大学选修哪些通识课。美国大学对学生有通识课的要求,具体要求各校不一样,大体思路都是学生不论将来学什么专业,在低年级都要选修几门科学课,几门艺术课,几门历史课、文学、写作课,等等。
我的目标大学要求文学专业的学生至少学一门生命科学和一门物理科学 。生命科学课可以是“环境保护”,物理科学可以是“天文学”这一类软性课程。但如果我将来要学医学方向的专业,我就必须选医学难度级别的生物课和化学课。我在社区大学的时候选了医学类的生物课。那个学期为了满足转学要求我选了22学分。
事实证明生物课是最耗时的。我们每周要学两章。生词相当多,我读一章教材就需要一整天。再加上做作业的时间,基本上一周有三天要耗在这一门4学分的课上。
由于时间冲突,我没有来得及在社区大学选化学课就转到教会大学去了。在教会大学的第一学期,我的学术导师想当然地替我选了“化学与社会”。我一听就表示嫌弃,分明是文科生混学分的。
我要挑战自我,选硬核化学。
可是由于技术原因,这门课我一直没选上。我校的医学类化学课都开在离本部几英里外的护理学院。连续三个学期,我总有一门文学系的必修课紧挨着化学课,而我无法在十分钟之内赶到护理学院去,或者在十分钟内赶回本部来。
到了三年级的暑假,我无论如何要选化学课了。放假前,学术导师提醒我:还差一门化学课,不然毕不了业。我不假思索地说:在咱们学校总是选不上,我打算暑假去社区学院修课。经过三年的学习,我已经修完了80%文学系的必修课,也早就把医生助理的梦摒弃了。即使这时我选了医学类的化学课,也不可能转去学医学助理了。但我出于惯性思维,仍然在社区大学选了医学类的化学课。
社区学院的化学课开局就各种不顺。主要是实验部分特别琐碎,教授的要求特别多。这门课的实验部分是从学校领来仪器设备,学生自己在家里做。很多同学到了截止期当天才开始做实验,如果这时发现学校发错了仪器,那么实验就不能按时完成。但是教授毫不通融,而是反问“你为什么不早点检查?为什么不能及时发现早点解决?”有一次我忘了参加一个网络讨论,就给教授写邮件道歉,请他把讨论版打开,让我把发言补上。诚恳道歉通常都是管用的,教授一般都会允许补交,但是会扣掉百分之几的分数。然而这个教授压根儿不理我。
我感觉这个教授特别像文革电影里的“反动学术权威”,自以为掌握着一些科学真理就趾高气扬爱谁谁,和我们文科教授谦恭有礼视学生为客户的作风截然不同。
真正给我打击的是期中考试。我自我感觉学得还不错,艰深的原子理论都能理解。但是期中考试题目的很大一部分是单位转换,而我一向以为这是实用领域的知识,用的时候查一下手册(或者上网搜一下)就行了,于是没有复习。
我的实验也被扣了很多分。教授总是嫌我的数据误差太大。可是,数据准确很重要吗?理论上我完全知道刷了试管以后,如果试管不干,可以用吹风机吹干。考试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步骤写清的。实践中我只是懒得吹干而已,重量不就是多了0.01克吗?我最不耐烦的是等实验结果。在化合物慢慢反应的间隔,我完全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感觉时间白白浪费了。
有一天我实在没有耐心等,就打算编造数据。我手拿计算器,按照理论倒推数据的时候,忽然感到自己十分可笑:这是何苦呢?如果当初选了“化学与社会”,估计只需要背一背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就可以了。
这件事让我反思:我当初为什么想学医学助理?是为了挣钱。可是,我能挣得了这份钱吗?我的性格、爱好,早已经决定我当不成医生助理。能让我激动的瞬间,永远是想到一个精妙比喻的时候,绝不是得到一个精确数据的时候。如果把学习概括成格物致知,我的思维方式早就定型成只爱致知,不爱格物。
我只是一直还保留着错觉,认为自己还有选择。
当然,从积极的角度想,我因此而理解了美国通识课的重要。通识课的设立,就是让学生把各个学科都体验一遍,从而更直观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蛮横的教授,就是未来医生的预演。
做医生助理就得听医生的,哪儿像文科系统里凡事儿好商量?
做医生助理就得在实践中快速反应,人命关天的岗位怎能雇一个高谈阔论原子核结构,拿到处方后还得查手册计算质量的人?
不在化学课里碰壁,怎么知道自己只能当作家?
每当在学校遇到新同学,需要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总是说:因为我的孩子在美国上学,所以我也想来体验一下美国的教育。如果他们问我体验到了什么,我就会说:拿GPA4.0真是不容易。我在社区大学拿了三个B。一个是化学,一个是英语101,一个是哲学。这三个B,除了化学是水平不够,其它两个都另有原因。
教英语101的老师特别琐碎,留的作业又多又杂乱无章,一不留神就忘了一样。还有就是互相改作业环节。分配给我的同伴不把他的作业发给我,我就没法批改。但老师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你没有上交给别人改过的作业,你就没有分。
哲学课的B是因为我期中考试得了60。那个考试是线上开卷考试,按理说抄也能抄个A,结果出了意外。线上考试通常的截止时间都是考试当天半夜12点,偏偏那个老师把截止时间定成了考试当天下午四点。我事先没注意到,下午三点多才慢悠悠地打开电脑,准备答题,这时即使抄也抄不全了。
可见保持GPA4.0是多么不容易,需要多么执久的努力且注重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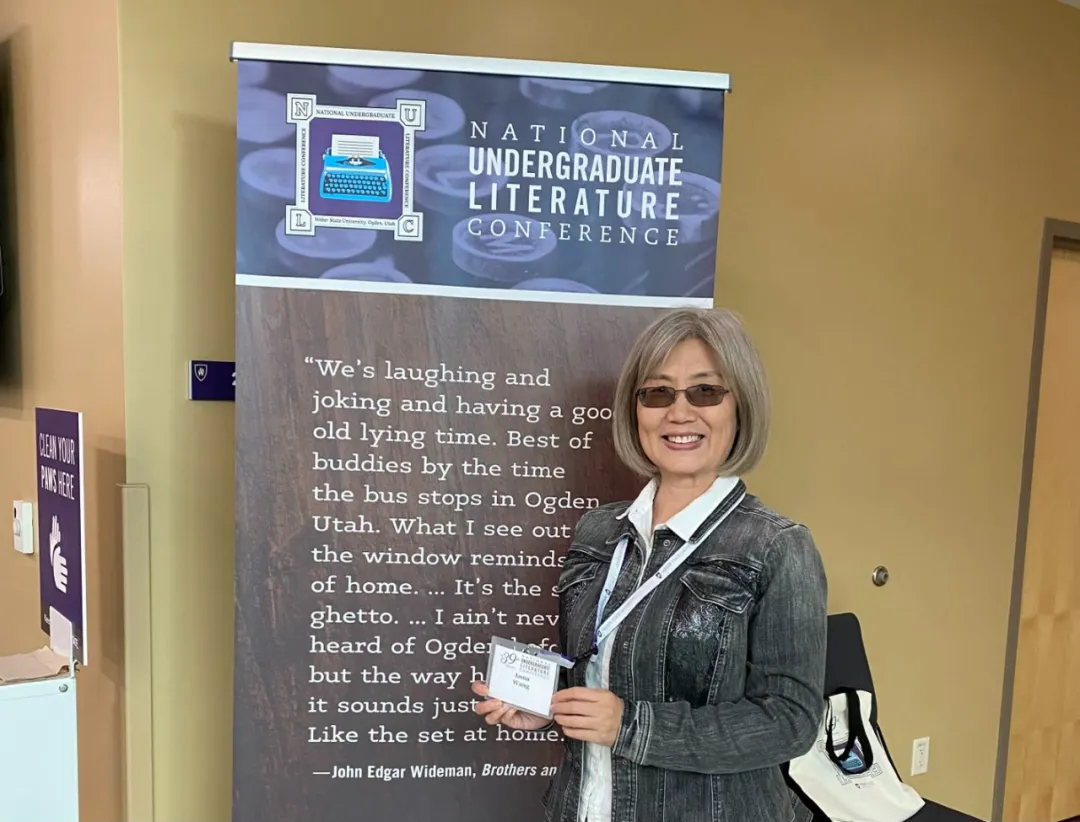
我的论文入选了全国大学生文学专业学术会议
我的同学们都是我的孩子的同龄人。听到我的回答,很多人都说:你真是个好妈妈。听了这样的夸奖,我感到非常惭愧。相信我,主观上我总想把自己描述成好妈妈。但实际上我可能起过很多反作用。
我不理解学习需要热爱,总是强调用功。比如我会跟孩子们说:当年我高考的时候,连写名字、学号、考号这些都是反复练习,争取控制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在我的理解中,学习是苦差事。他们成绩不好,我就说他们不用功。
他们不承认自己不用功,就解释说自己是真不行,久而久之他们就形成了自己真不行的认识。我两个孩子在上了大学后,都有一个瞬间,突然发现:“原来我不笨”。他们跟我描述的时候,我还表现得很不耐烦:“早就告诉你了,你不笨,你就是不信。” 但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发现自己的重要性。每个人都需要经历发现自己的过程,妈妈再好,也不能代替孩子完成这个过程。
我的上学过程,也是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
我在圣地亚哥社区大学的一年半学生生涯中,只上过一门面授的课程:数学121。有了面授课,就有了到办公室请教问题的机会。有一天,我成了当天最后一个来请教的学生。答疑结束,教授和我一起离开。我看着她关灯、锁门。门是玻璃做的,即使关上我也可以看到办公室的布置。办公室的灯关了,但是随即我们的脚步声就唤醒了走廊里的声控灯。在淡淡的走廊灯光下,我回头看到了教授桌子上摆着的一个相框,里面的照片似乎是她搂着她的孙子孙女。
这位教授比我大几岁。如果我在街上遇到她,可能会认为她只是个普通的奶奶。没错,她是个奶奶,但她还有另一种身份。她有一间办公室。
这个场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所有学习文学的女生,都知道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言:女人要想写作,必须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我一直都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并没有取得我自己理想的成就。我需要的是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不是家里的书房,而是在一个工作场所里的办公室。
我上学是因为我不能自学。我必须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学习社区中。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但自由职业只适合那些有强烈信念和自律的人。对我来说,自由职业是一个陷阱。我讨厌一些人把自由职业者视为家庭主妇的委婉说法,但我经常躲在这个含糊的术语后面,只因为它很方便地给了我偷懒的借口。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上学不光为了能用英语写作,还为了毕业后找到一个当教师的工作。很多人都跟我说:学写作不需要上学。这是对的,但是当教师就必须要上学。要想进入体制,就要拿到相应的资质。
你看,我在大二的第一学期,就明确了上学的目的,可是一年前以后,我仍然选了硬核化学课,似乎我还没完全泯灭学医生助理的愿望。毕业典礼上,我仍然表示我上学是为了和孩子们沟通。这种表述并非全然说谎,总有真实的成分在内,虽然绝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归根到底,我总是认为只有为了孩子做事才是说得出口的理由。这种思维模式妨碍了我自己的发展。我自2007年移民加拿大以来就一直想用英语写作,但我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这让我现在感到后悔。一个人的知与行之间往往有很长的距离。如果我当时更加坚定,并且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识,我本可以走一条直路,但是我没有。
幸运的是,天上始终有一颗星,即使我没有抬头看,这颗星也在指引着我,让我沿着地上的曲折道路将近天上的星辰。
我的人生之路不完美,但我好歹还算是朝着自己的目标蛇行了。我的育儿方式也不完美,所以我才经常反思中。
<End>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