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黄连着土黄,在越野车窗外流畅衔接着。人的精神和身体都被卷入其中,在高反的作用下有轻微的麻醉感。
从喀什市区出发,去往更南的南疆。需要沿中巴友谊公路,国道314,稍稍往西北,去往红其拉甫口岸的方向,经过旁边的克孜勒柯尔克孜自治州,我们的目的地是全国唯一一个塔吉克族自治县——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人是欧罗巴人种,像欧洲人一样金发碧眼。他们的语言是波斯语,但是他们和伊朗的联系已经很遥远了。我们车队的一个司机就是塔吉克族男人,大家都叫他“老胡”,从他名字发音的第一个字而来。他说自己曾经参演过姜文的电影,在里面饰演一名苏联军官。他有着欧式的俊朗面容,发型像是退役的法国球星吉诺拉。在他们族人里,他的普通话算是不错的了。
我从小就喜欢读关于西域的研究。那些繁复的国名和地名于我非常遥远,但却有内心的牵引。葱岭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地域,因传说山地上布满野葱而得名。唐玄奘经此去印度取经。而当它变成“帕米尔高原”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一个卷入近代政治纷争的地名。在其乐16岁这一年,我带他去往一个我在少年时格外好奇的地方。

这已经是我和其乐的第五次父子单独旅行。从纽约到印度,从旧金山到香港。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乐也是。他先是在2019年9月到英国留学,因为疫情又在今年初转回国内的国际学校。从去年开始,他的个头超过了我,脸上长出了不少青春痘;rap成了他的日常,嘴巴里经常念念有词地练习着,对于世界依旧天真,却对最诡谲的政治和历史感兴趣。
喀什老城的街道,正在旅游业复苏中慢慢变化,有了几家在其他城市随处可见的文艺咖啡店,手工艺品摊上满是可以在身上敲敲打打的木头制品,其乐淘到了一把胡杨木做的弹弓。一家婚礼旅行门店大门紧闭,可以想见艰难时刻还没有过去。网红风格的民宿开始蔓延到小巷里,本地向导说接下来一年这一大片民居都将变成民宿,这是让一些人开心一些人伤心的发展。

在那些没有通道的小巷里,维吾尔孩子的眼神非常清澈,他们尽兴地拿着手里的水枪互相喷射。老城里不通汽车,孩子们可以在巷道里互相串门,玩耍,还有一些小秋千可以荡漾,像极了八十年代我们的成长环境。这令我羡慕,也令并没有经历过这种氛围的其乐陌生。
“如果你想研究人类学,可以来这里租一个房子,住三个月,天天和他们泡在一起。”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向其乐提议。
其乐不置可否。他正处在开始探索自己未来的专业和兴趣的初始阶段。十六年来,他在学科上基本上是无欲无求的。但现在,学科的要求标准突然即将和他接下来几年的生活去向接壤,这让他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上若有彷徨。

这一代接受体制外教育的孩子,有很多是活在当下的。物质的充足让大脑皮层细胞不会倾向于去思考未来。在一些天生小聪明的作用下,偶尔的一些考试关口也跨越了。如果没有痛苦的煎熬,人生自然未能那么深刻。
我想起16岁的自己,在广东四线小城潮州的老房子里,准备着几个月后即将到来的中考。虽然大概知道自己应该能够通过考试留在这座本地最好的中学,但是对“万一”的担心,也有对名列前茅的期待,让我压力很大。半夜,窗外在装修的隔壁小区,脚手架还没有拆,一个水龙头汩汩地流着水。我开始持续地失眠,不知道是因为那水声,还是无法安放的情绪。
那个时候,我们的阶段目标是线性的,从好的初中去往好的高中,学习和考试的内容都是被安排好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在高中我唯一需要作出的选择是选理科还是文科,然后朦胧地选择大学志愿,去往我们没有一丁点现实接触的大城市继续求学。

而今天,对于一个体制外路线的16岁孩子,他们要做的选择太多了。或许包含了IB还是A Level的选择,不同的中学,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学专业,以及要申请它们所附带而来的种种要求:学科成绩、标化成绩、个人项目、活动、自述、经历……
中国孩子现阶段的教育选择是两个极端。
应试教育的“分数决定一切”使很多孩子根本不需要接触外部世界和思考未来,要先拿到“分数砝码”才能有充分的选择权。
而对于体制外,特别是选择美国方向的学生,要准备和选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们需要在尚且有些懵懂的年纪,去做一些显得自己已经对人生有些规划的证明,讲好一个故事,同时还要接受之前显得陌生的分数标准要求。很多孩子并不像留学机构包装的“牛娃”一样都非常有自主思想,懂得如何时间管理,能有条不紊地安排一切事项。
像其乐,去年的大部分时间,他还在伦敦思考学校所教授的知识是不是无用。在去英国读书的时候,他降了一级,然后发现不需要怎么努力,成绩也名列前茅,这让他产生了一些错觉。他还没有接触到A Level核心的课程和要求,却被一场疫情席卷回国,回到IB体系,并骤然需要面对一年后开始的大学申请。
不管怎么样,他还要继续认知世界和社会,才能在一片纷繁中初步做出人生方向的选择。
我们的旅行又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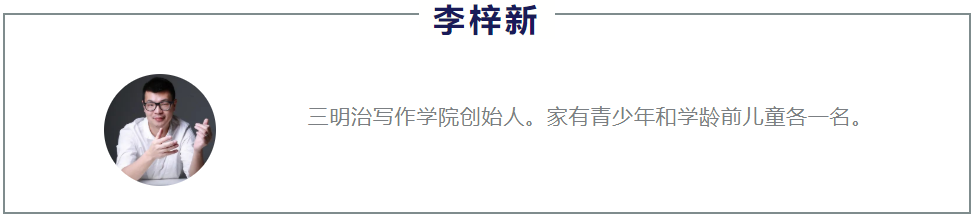
— END —
 菁kids上海
菁kids上海
国际教育 | 家庭生活 | 社区活动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