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道道
图|来源网络
到了年底年初的时候,阳了反倒让人如释重负。
难受上几天,身体就有了金钟罩,再不用战战兢兢地出门,见谁都疑神疑鬼。
三年了,阳光底下横着走的日子终于又回来了。
我感染的应该是“懂事株”。它知道我不光要经受身体的痛苦,还要扛住心灵的打击,所以每一种症状都是点到为止,并不过分死缠烂打。
都说每个家里都会留一名“天选做饭人”,感染的都是“迟到早退毒株”,能错开时间来料理一家子的吃喝。
像我家队友就只发了一天烧,跟久仰的新冠病毒都没来得及好好厮缠一番,就下床担当起了“牧羊犬”的光荣使命。
做饭这件事,上半年封的时候都是谁会做谁做,下半年阳起来却多半是不会做的也要做。
奥密克戎堪称全民厨艺普及运动急先锋,从年头到年尾,几乎把每个成年人都按进厨房里集训了一轮。
相比此前,年底这波做饭人因为集合了火线上岗、舍己为人、临危受命等要素,更容易被载入家史流芳百世——没人会忘记这场世纪大疫破门而入时,是谁填饱了一家的肚子。
就像公司里的“天选打工人”,老板可能会忘记发奖金,但不会忘了谁是战斗到了最后的那个“王成”,扛住了领导客户所有的火力,让公司不至于关门歇业。
我家的“做饭人”同样让我刻骨铭心,只不过记忆的内容有点一言难尽。

第一天烧刚起时嘴里没味,我想喝口甜甜的稀粥。考虑到他照顾病人没经验,我只叫他抓一把小米加一块红糖煮点粥。
小米粥是最简单的了。随便把米放水里坐火上搅搅,很快就水米交融,比大米粥好掌握。整个操作的难度系数大概略高于把自来水烧开。
我烧得辗转反侧等着这最简单的一口,端来的却是一坨黏糊糊湿哒哒的小米饭。
“什么呀这是?”
“不知道,煮着煮着就干了。”
“这么干怎么吃啊?”

三分钟后,一大碗小米汤放在我面前,清汤寡水底下沉着一坨小米。水和米一看就不是原配,彼此都是一副瞧不上对方的样子,吃到最后一口还是各就各位。

第二天家里没小米了,那就换大米粥,我也不想他为了把米再出去跑一趟,有啥吃啥吧。
结果拿到手是一碗更干更烂的大!米!饭!
???
一个人怎么能在同一件事上连错两次?
“不知道啊,煮着煮着就胀起来了,然后又干了。”

我已经不敢嫌干了,不然又会变成一碗寡淡的水泡饭。因为他对付太干的办法就是咣咣加白开水。
你要再不满意他还不乐意了——要粥给煮粥,嫌干给加水,还要我怎么样?
这天下午我挣扎着去厨房找吃的,这才终于破案。

你见过用巴掌大的小奶锅煮粥的吗?还一煮就是一天的量。米粒别说在水里头自由地翻滚,估计连翻个身都费劲,都是活活憋熟的吧。
你咋不拿脸盆泡澡呢?
这天晚上,他又要给我吃憋熟的烂米饭。我忽然想起自己高烧两天了还没有吃过一点盐分,很容易电解质不平衡。
没错,摊上这种糙汉,连这样的基本常识都是需要病人自己领悟的。

你昨天给他输入过“加一块红糖”的命令,如果不主动撤销的话,他就能每天一模一样地执行下去……
我只能说我昨天想吃红糖不等于天天想吃,我现在发烧需要补充盐分。
他把碗往我手里一墩,转身拿来一包薯片。
那么费事干嘛,直接抓把盐来倒我嘴里不更省事?
直男的脑子是做了部分摘除术吗?

第三天,我跟他说想吃面条了。
傻子都知道,发烧的人要吃的面应该是融在面汤中煮得绵软稀烂不用嚼就自动滑进喉咙里的那种,只消几滴油星两片青菜开胃提亮,江南人所谓笃烂面是也。
我家傻子不知道。

他端给我的是一大碗浓油赤酱的干拌面,有肉没菜,有面没汤,油光鉴人,面都还是刚断生的,泛着惨白色,嚼起来颇费口舌。

这哪像病号饭?这是给扛长活的精壮吃的啊。
不用说,又是煮着煮着就干了。
发烧三天,除了第一天那碗二婚的小米汤外,我没吃到过一顿有汤水的饭食,每一碗都实诚到吃完就能去蹦迪,每一口都让我边吃边想妈妈。
再这么下去,不烧死也要气死了。

端着半碗干不动的面,我终于忍不住问:
“天天说太干了太干了,你就再算再没常识也该知道发烧的病人需要吃有汤水的东西吧?怎么我就是等不到一顿能吃的饭呢?”
他回答得理直气壮:“你就不能坚强一点吗!”
“好好好,下回生病我先给你拿个大顶碎个大石,然后你给我弄口人吃的东西行吗?”
“行”。

老实说我还挺羡慕那些端着菜板到老婆床前讨教的老公,一张白纸教啥就是啥。不像我们这位,仗着能应付一日三餐的那点手艺,他觉得自己就是厨房里的王者——你连辣子鸡都不会做,凭什么教我做病号饭?
结果就是看起来要面给面要粥给粥了,可是你想要的眉清目秀,都让他整成了残花败柳。
朋友们看到我的病中伙食,都说恭喜恭喜,胃口这么好说明快好了。
只有我无语泪三行,哪个发烧头痛嗓子痛的人吃得下这个?

可是家里就这一个仅存的牧羊犬,直到我退烧都还闹不明白病号需要吃点什么。
大家都在坐月子,我家怎么把个抡大锤的给当成了月嫂呢?
— EN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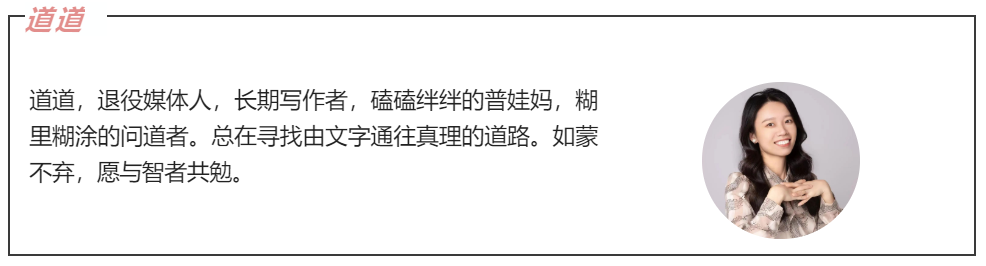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