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代孩子都有不同的命运。
儿童节,也许你会带着孩子出入精致的亲子餐厅,在迪士尼挥霍一整天,或是送ta一份节日礼物意思一下。这一代孩子无疑是极受重视的。而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儿童还要为家庭经济做贡献,“无忧无虑的童年”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
不过,魔都孩子身上的学业负担也不轻,这或许就是他们这个时代的命运。在痛斥“鸡血”的舆论和孩子们愈发紧凑的时间表之间,为人父母的,究竟该如何看待如今培育孩子的方式?
今天这篇文章中,作者柒拾介绍了《不平等的童年》一书,该书从社会学角度来观察不同阶层的孩子如何受教育和度过闲暇时间,分析这其中的不同会对孩子们长大后有怎样的影响。从自己童年被“放养”一路走来,到现在女儿出生要决定如何培养她,柒拾从本书汲取的精华,也分享给您。
文 | 柒拾
图 | www.pexels.com
在各种中产育儿乱象之下,聊到孩子日程安排太满时,常会听到一个说法,“应该让孩子们像过去那样有很多闲散时间自由地玩耍”。其实这只是一个浪漫的盼望。看看我的父辈们,从四五岁就开始分担家里的劳动。事实上,历史上一直要到二战后,生产力的发展加上童工法(1920年以后)的实施,孩子们才开始有很长时间自由玩耍。
然而在那之后,“课外活动制度化”随之形成。特别是在中产阶级之间,孩子们很快“再度”失去自由玩耍的机会。与之同步酝酿的,是家长之间普遍存在的焦虑感,挥之不去。
几乎每个父母都在纠结:我如何能给孩子最好的东西(生活、教育、环境……)?说到最好,就难免涉及社会阶层的话题了。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里,除了一些带实验性质的小范围乌托邦,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平等的。想到我们家刚实现的“菜场财富自由”,很明显,虽然我很爱女儿,但是给不了她“最好”的成长环境。
那么问题来了,社会阶层的不同,对育儿果真有那么大的影响吗?带着这个问题,我拿起了Annette Lareau 《不平等的童年》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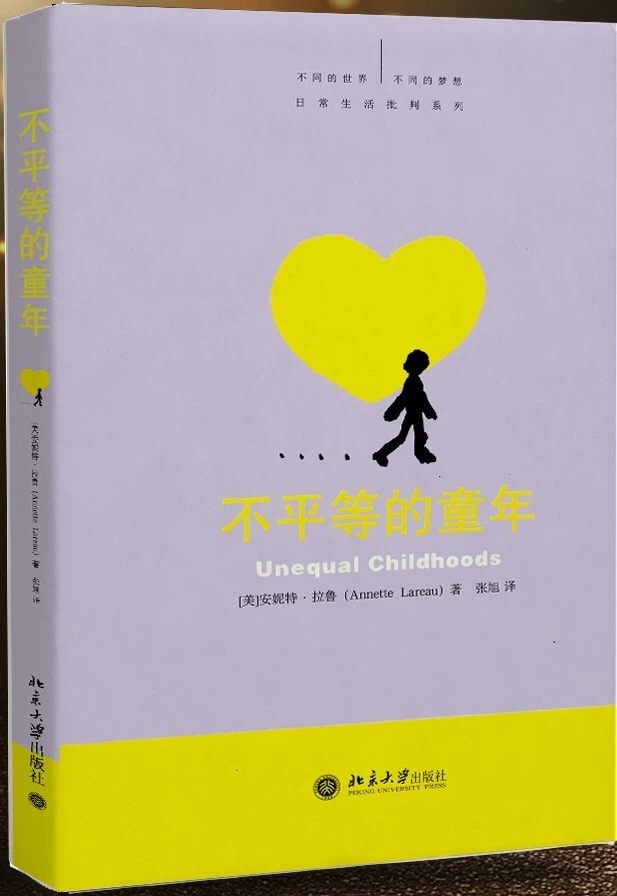
《不平等的童年》
作者: [美] 安妮特·拉鲁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
原作名: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译者: 张旭
出版年: 2009-12
这本书源于一个持续了8年的研究项目。作者招募了88个家庭(都是职工家庭,不包含自己做老板的情况),根据父母工作场合的权威力和“文凭屏障”(有些工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凭才可申请),将这些家庭的孩子分为三个阶级:
一、中产阶级儿童:父母(至少一方)在工作上拥有管理实权,或者其工作需要非常复杂的、有专业证书(通常是大学文凭)的技术。
二、工人阶级儿童:父母双方都不拥有中产阶级类型的工作。这个类别包含底层的白领。
三、贫困儿童:父母接受社会救济,且没有稳定而持续的工作。
通过对这些家庭多次、长时间、深入的观察和访谈,作者试图“展示一幅透彻而真实的家庭生活画卷”。
本书聚焦的领域是:孩子们如何度过闲余时光,父母如何与孩子在语言上交流,如何惩戒孩子,家庭社交圈的特点,如何与公共机构(比如学校、医院、政府机构)打交道。基于这些观察,作者发现阶级在教养孩子上产生的作用是显著的,其中,中产阶级善用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则倾向于成就自然成长(the 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
根据这个定义,我和太太都是典型的自然成长,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但如今,我们和身边的同侪不约而同倾向使用“协作培养”的方式养育下一代。当然更多时候,我们可能将其称为“科学育儿”,或“做更负责任的父母”之类的。
有趣的是,选择协作培养往往是不自知的,仿佛有种神秘的力量作用于其中。我们通常并不会意识到自己“选择”了协作培养,这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过程。
近距离接触过两种养育方式,我读这本书时有种特殊的代入感。在我心里萦绕了好几个问题:协作培养是否真胜过自然成长?父母对孩子生活的干预程度应该有界限,但那个界限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可能人以群分)会不自知地倾向协作培养?为什么现在奉行协作培养的我们心里总是充满了焦虑?

想起今年过年离开父母家的前一晚,我和太太打包完行李特意到楼下陪老人聊天叙别。不可避免地聊到二胎话题,聊到现代社会养育下一代需要的资源与心思。我老妈表示理解,一心希望再添个孙子/女的她还是发出疑问:我们养你时也没那么多花头,你不也长得蛮好的?现在养个孩子花那么多心思,也不见得一定有什么功效,关键还是看每个小孩自己的天资。
1
自然成长的幸福童年
我的小学是当时典型的乡村小学。“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这种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并不是玩笑。
一年级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的老师是一位刚从初二辍学回来的大女孩。当时一个班级只有一个老师,教所有的科目。大女孩带着一班小屁孩整天疯玩。直到学期结束前两三周,突击把教材过了一遍。
当时身边的大人们甚至还没听过除了自然成长之外的其他养育方式。只要不闯祸、不被告上门,没有人身危险,家长通常是放任自由,完全把孩子交托给学校。小学第一年,我可以说是完全自我放飞的。
所以我有大量的时间自己安排。我总是能找到乐子,也总是能找到小伙伴(很多是堂/表兄弟姐妹)一起消磨时间。我们大多游戏都是就地取材。如果有个空地,划个圈子,我们就可以组队玩追赶游戏及其变种。如果哪家建房子,有堆沙子,我们就在上面玩洞,投弹珠,盖房子,也可以消磨半天。如果有谁搞到一块磁铁,我们就拿个塑料袋裹住,然后趴在地上四处收集细细的黑色铁沙,直到几天后拥有足够多的铁沙制作磁力画板。哪怕什么花样也没有,也可以四五个人围成一圈说些无意义的话,并不无聊。
因为在共有空间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我和(堂)兄弟姐妹建立了很紧密的联系,这些关系一直到今天还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安慰。我有个大我三岁的姐姐,虽然会有彼此厌烦的时候,但没有过现在中产阶级二胎家庭里常见的老大和老二的那种竞争与冲突。
与之相对的,作者提到中产阶级孩子说“恨”家里的某个兄弟姐妹是很常见的,而且听到的人也不会作出什么特殊的反应。这种兄姐妹之间公开表现出来的敌对行为,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中却并未出现。作者猜测部分原因是,中产阶级的手足之间存在对资源的竞争,而另外两个阶层的孩子之间更多的是彼此的陪伴和依靠。
自然成长与协作培养的碰撞
从小学三年级起,我开始喜欢读文字。当时能找到的课外书也就几本:姐姐留下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爷爷私藏的面相&风水的书(繁体,竖排,毛笔字抄写),还有几本中药偏方。当时完全不知道可以找大人提供更多的书,也不觉得大人应该满足我的需要,甚至大人们也不关心我在看些什么(不代表他们不爱我)。
如同本书描述的,我这是典型的自然成长:儿童的世界和成年人的世界是隔离开的,儿童不受干预的自己游戏和长大,并渐渐对陌生环境,对权威发展出一种局促感。一直到多年后初入职场,面对难题时我还是习惯咬紧牙试图自己搞定,但其实我本可以从资深的同事那边得到帮助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相反的,在中产家庭的协作培养中,孩子需要参加许多由成年人组织的活动(培训班、体育项目等等)。这些活动在组织风格上都复制了工作场所的关键方面。所以孩子们十几岁在里面学到的技能,就能帮助他们成年后在初次工作时继续受益。比如每参加一个新活动都会见到一批新的成年人,可以学习怎样与他们共事。

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就没有类似的机会接受“就业前训练”,他们很少得到在正式场合下联合协作的训练。再比如宽广的视野,再比如根据主次安排活动的能力(因为中产孩子因活动较多而产生了冲突,所以有机会操练这种能力)。这些技能都帮助他们成年后更容易适应职业要求和社会的需求。
对我来说,在进入职场前就经历了这种生活状态的变化。高中时有机会进了当地的名校,身边同学大多是一路接受协作培养走来的。前两年的不适应和艰辛,有很大部分源自自然成长者与协作培养者主导的世界发生的碰撞。幸运的我在碰撞中渐渐适应,但也有不少类似经历的同行者在碰撞中渐渐自我放弃。
虽然两种教养方式都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了不同的优势和负担,但是孩子在其中训练到的技能却被社会赋予了不同的价值。
在学校、医疗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场景的世界里,自然成长者们在自组织活动里学到的技能与独立性,无法像中产阶级家庭中强调的说理能力、联合协作能力那样被转化为同样的优势。简言之,我们的社会运作模式更倾向于给通过协作培养所生成的能力投赞同票。
这就是中产阶级孩子获得优势的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我们和身边的同侪(经济和精力在基本生活所需之外还稍有余力)往往不自知地倾向协作培养的原因。
3
协作培养的迷思
有趣的是,虽然在协作培养里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但是家长在这过程中并不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当下的魔都,父母更多是被主流思潮、商业机构携裹前行。
那么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可以如何自处?这是个因人而异的问题。每个家庭都很特殊,都值得探索自己的家庭核心价值观。要不要参加某个活动,要付出多少代价读什么学校,这些决定都应该源于这个价值观。如果所做的努力和付出没有由心而发的力量,就很难陪孩子喜乐而坚定地享受过程。
当我们需要在缤纷的选择里做决策时,这份内在的笃定会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得知道,每个决定都有其收益,也有其代价。比如本书中提到的父母与孩子之间对话的语言模式。
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普遍存在一种模式:和孩子商讨事务时大量使用语言,也通过讲道理引导孩子遵守纪律。这些对话:“帮助提升孩子的词汇量,熟悉在课堂上及其他与成年人打交道的场景经常会碰到的语言交流方式……学校要求孩子们懂得如何以理服人,医生更愿意病人能够见多识广。”
但同样是这些技能,也可能会造成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要跟家长据理力争,挑战或拒绝父母的权威,让家庭生活疲惫不堪。相反的,自然成长的孩子里,父母更少与孩子大量对话,比较多是简单的指令,这些孩子更多会养成恭敬有礼、不抱怨、不激怒或纠缠父母的习惯(当然有其代价)。
但是,在这个社会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确实更难找到锚点明晰自己的内心,也更难对现状怀有安全感。中产父母们的焦虑无孔不入。焦虑并不能打败焦虑,我们需要更聪明地制定作战方针。
作者给中产阶级们的建议是,家长要制定明确的界限:减少孩子参加活动的数量,安排全家在一起的时间,优先考虑家庭活动而不是孩子的课外活动,并在总体上把群体的需要放在个人需要之上。
作者同样建议,在和孩子的关系里也得设立界限:鼓励家长找回自身固有的力量来自己做主;在有些事情上给孩子明确的指令(而不是完全当作朋友,一味地说道理);顶住诱惑,不去寻求孩子的赞同。
仔细看一下,这些建议的很多要素正来自自然成长,记得在协作培养的基础上更理性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明确投入的方向和程度。
如同本书结尾所说:
这并不是要我们怨天尤人或者沾沾自喜。而是坦然承认自己当下所处的阶级,然后把所拥有的资源配置在家庭成员一致认可的方向上,并一起承受这些决定的代价。
重点是,你们家找到一致认可的价值观和方向了吗?
-End-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