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总觉得差点儿意思, 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不充实不快乐?对现状和自己不满?好像都不是,好像又都有一点。我时常一边认同肯定自己,又一边隐隐地反抗和逃离。 把家搬到瑞典,给我一个绝佳的机会重新开始。我又走进了课堂。这一次不仅仅是为了谋生充电,还为了到大学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和享受读书的乐趣。
专栏作者:桂桂
转眼到瑞典已经三年。离开北京时,带着对新旅程的期待,我计划着在异乡从头再来。 回想自己的人生经历,生于1980年代初的我,大概是我朋友圈中长辈最爱的“四平八稳”的表率。从省重点到211,从四线小城到首都,本科四年一等奖学金,保送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字号体制内工作,结婚,生子。看上去该完成的大事都完成了,而且似乎还完成得不错。可我总觉得差点儿意思。 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不充实不快乐?对现状和自己不满?好像都不是,好像又都有一点。我时常一边认同肯定自己,又一边隐隐地反抗和逃离。 把家搬到瑞典,给我一个绝佳的机会重新开始。我又走进了课堂。这一次不仅仅是为了谋生充电,还为了到大学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和享受读书的乐趣。
艰难的起步
掌握流利的瑞典语是计划中无法绕开的第一步。来这边不久,我就申请了当地komvux(成人教育中心)的瑞典语课程。经过三个月的等候,我便开始到校上课了。我申请的SFI课程是Swedish for immigrants的简称,结课后有全国统考。考试通过相当于土著小学毕业水平,可以继续申请高阶课程。当时,我被分到SFI C级课程的其中一个班,学员有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而且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C级课进度很快,一周五天,每天授课4小时,还有一定的课后作业。虽然是学语言出身,但上课第一天我就被狠狠虐了一把。
老师Eva是出生在中部Smaland省的瑞典人,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从见面第一句话开始就完全使用瑞典语,而且语速很快。Eva禁止大家用英语交流,就连提问也规定必须使用瑞典语。对于只会说Hej(你好)、Tack(谢谢)和Hejda(再见)的我来说,第一天下来连蒙带猜,有点儿找不着北。这一天对于我来说太颠覆了。从初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法语,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拿着中国人写的课本、跟着中国老师学。我所熟悉的教学,无论听说读写,本质上都是在“翻译”。老师教的每一个词、句,都给你对应到中文上。突然间,中文不再是课堂讲解的介质了,甚至英语也不是——我仿佛成了不会游泳却被扔进泳池的旱鸭子。
还记得那天的话题有一项是谈论职业。在与我一对一的问答中,Eva指出我对programmerare(程序员)这个单词的发音不准。她纠正了我好几遍,但效果都不好。 瑞典语讲究长短音,如果弄错,听众不仅可能听不懂,还可能发生误解。programmerare的长音在第一个e,而字母r的发音需要弹大舌(Eva的口音很接近北部发音,但其实按照隆德所在的Skane发音习惯,r弹小舌,很接近法语r的发音,对于我来说驾轻就熟,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我根本做不到。在发r音的挣扎中,我几乎顾不上长音和短音的区别。
第一天课后回家,我很沮丧。但是以我的经验,语音对一门新的外语来说尤其重要,绝不能欠账,否则后患无穷。我振作起来,一边和孩子玩儿一边开练。做饭和洗澡时嘴巴不闲着,光programmerare一个词就被我念了上百遍,直到舌头变得特别听话。第二天上课,头天的词句我都能应付自如。 我打从心里接受并喜欢上了Eva的教学方式。很快,我就发现能听懂的内容越来越多,学习步入了良性的轨道。
给自己加油
因为SFI是免费的,所以很多学员并不珍惜。结课时,同班同学的面孔换了大半,有的人只出现了两次就再也没来。但是我告诉自己坚持下去。我把日常所有能开口的机会利用起来,包括买东西,跟幼儿园老师交谈等,假装完全不懂英语。上SFI的第四个月,我没有申请翻译(尽管可以免费申请),独自参加了老大的第一次家长会,用瑞典语跟大家交流。此后也一直这么做。 十个月后,我顺利通过了SFI的考试。接着又通过了SAS(Swedish as second language)第一阶段的考试(相当于高中一年级)。2016年,我因为二宝的到来暂停了学业。现在,我再次回到课堂。 距离完成我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但对我来说,能在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后从零开始,是挑战,更是幸福。
桂桂 GRACE GUI
80后妈妈,有一个属兔的儿子。大学曾研习法语和国际新闻,做过媒体记者、编辑,曾任《菁kids》杂志副主编。2014年迁居瑞典。现为自由撰稿人,译者。2016年4月,二宝出生。
*编者注:因为学业的缘故,桂桂将暂别《菁kids》,我们期待她顺利完成学业,重新和《菁kids》的读者再见!
本文原载《菁kids》北京版2017年3月刊,购买杂志,请点击链接,或扫描下面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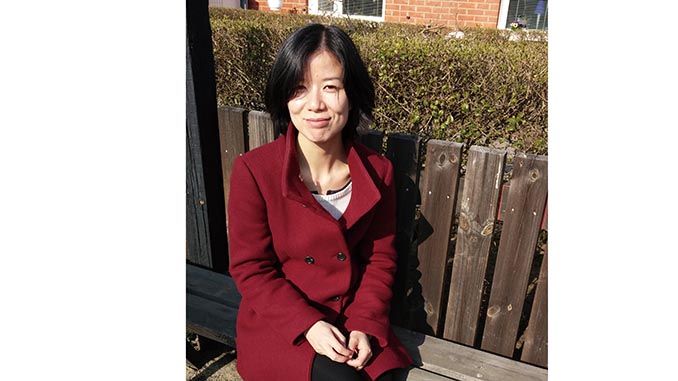
Leave a Reply